这就是事情的全部
比利决定一有机会就把手里的球送人。距离比赛开始只剩几分钟,球员们在球场上做热身和伸展运动,诺姆亲自带领B班走过大厅,在球迷面前露个脸,施展一下让人们神魂颠倒的明星魅力。在他的星光照耀之下,所有的怨恨、牢骚和路人的议论像板油遇到加热灯一样熔化了。嘿,诺姆!诺姆!今天我们能赢吗,诺姆?我赌牛仔队让三分,你可得帮我实现愿望,诺姆!他们所到之处球迷纷纷让路,犹如海水分开,手机的闪光灯此起彼伏,诺姆昂首挺胸,大步向前,对每个人都报以相同的亲切微笑。得克萨斯体育场就是他的地盘,他的城堡,不,是他的王国。真正的国王如今已经很少了,但在这里,诺姆就是主宰。比利发现要让下层人民开心太容易了,只要一个眼神、一次挥手、出现几秒钟,人们就像吸了强劲的明星牌白粉似的。
与此同时,比利在找一个小孩子,好把自己手里的球给他。不要有钱人的孩子,不要那种可以上电视、皮肤光滑呈古铜色、牙齿洁白整齐、手脚修长干净、脸蛋健康漂亮、尽显优良基因的孩子。不,他要找一个乡下孩子,瘦小,蓬头垢面,指甲咬得只剩一点,十岁左右,像条半大的小狗,浑然不知自己是个可怜虫。比利在找他自己。在一个汉堡摊前,比利发现了这么一个男孩,他个子不高,神情紧张,脑袋大脖子细,大冷的天却只穿了一件薄薄的棉连帽衫,脚上穿着一双破破烂烂的山寨锐步鞋。操,为什么他父母宁可花几百美金买牛仔队的门票,也不肯给儿子买件像样的冬衣?这些美国消费者的心理真让人恼火。
“抱歉。”比利一边喊一边走上前去,那孩子呆站在原地,不知所措——我该怎么办?他的父母转过身来,真是绝配,两个人都傻里傻气、呆头呆脑的,显然作为人类和家长都很无能。比利无视了他们。
“小伙子,你叫什么名字?”
小男孩吓得下巴都掉了,露出不健康的白色舌头。
“孩子,告诉我你的名字。”
“库格(Cougar, 意为美洲狮) 。”男孩终于说了出来。
“库格。那种动物?”
男孩点点头,不敢看比利的眼睛。
“库格!很棒的名字!”他在说谎,库格这个名字太可笑了,“听着,库格,这儿有一个签了名的橄榄球,刚刚在更衣室里,一群牛仔队队员给我签的。可我要回伊拉克去了,要是把球带去会弄丢的。所以我想把球给你,你觉得怎么样?”
库格壮着胆瞥了一眼比利手里的球,然后点点头。显然他在怀疑这是不是个羞辱他的陷阱,为了拉他内裤或往他背上扔鞭炮。
“那好,小伙子。球给你。”
比利把球递给他,转身离开,没有停留,没有回头。他今天已经受够了各种肉麻伤感,不想这一刻又变得煽情。曼戈刚才停下来等他。
“你为什么这么做?”
“不知道。就是想这么干。”回想刚刚的情景,比利虽说莫名感伤,但心里感觉好多了。两人默默无言地走了一会儿,曼戈把自己的球给了一个路过的小孩子。
“去他妈的签名。”比利说。曼戈笑了。
“要是他们赢得了超级碗,咱们刚刚可是把一千美金拱手相让。”
“是啊,哈,赌一千美金他们赢不了超级碗。”
仍旧没有中场秀的消息,只有诺姆的保证:“会让B班大显身手。”这有可能只是当你站在那里的时候叫你的名字,但也可能是恐怖而又艰巨的……难以想象。有传言说牛仔队老板的私人包厢里有好几个吧台。B班的几个低级士兵私下商量要喝个酩酊大醉,不过比利想到费森,偷偷把酩酊大醉改成了微醉。这是个一时冲动的邀请——到我的包厢来看开球!他显然患上了严重的B班病,这种“后方热心支援前线”的螺旋原虫让脱衣舞娘甘愿奉上免费的脱衣舞,让上流贵妇变得嗜血。B班队员们鱼贯而入时,屋内响起热烈的掌声,这些平时不过是礼貌、公式般地拍手的人竟真的在使劲鼓掌欢呼。B班威武!美军万岁!诺姆夫人站在门口迎接他们,就算她因为十位粗声粗气、满嘴酒味的彪形大汉涌进原本已经济济一堂的包厢而心中烦乱,她也很有涵养地什么都没有表露出来。
很高兴你们能来。有很多朋友想见见你们。比利扫了一眼包厢,蓝色地毯,蓝色的家具上点缀着些许银色,每面墙上都安装着巨大的平板电视,有两个吧台,冷餐和热食的自助餐台,有穿着白色西装的侍应生,往下走几步是第二层,跟第一层一模一样,再往前是一排排布面体育场座椅,阶梯式向下延伸至正面的玻璃围挡,可以俯瞰整个明信片般的球场。钞票的气息扑面而来,像模糊的嗡嗡声,或是唇间麻麻的薄荷味。比利心里琢磨,不知道财富会不会像细菌一样,一旦靠近就会被感染。
大家别客气,诺姆夫人轻声说。随便吃随便喝。不用再说了,夫人。B班已经全体准备好冲向免费饮料了,戴姆在一旁狠狠地瞪着他们,做着“就一杯”的口型。不过士兵们开始前,诺姆先站上一把椅子——他就那么喜欢椅子?——又开始讲话,他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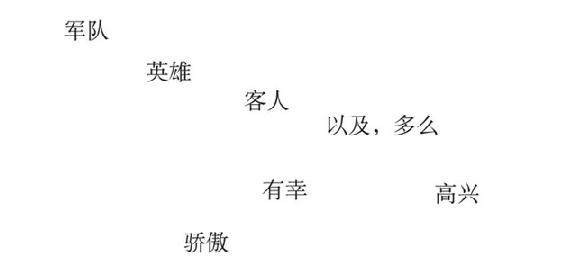
奥格尔斯比家族能在感恩节这天,有机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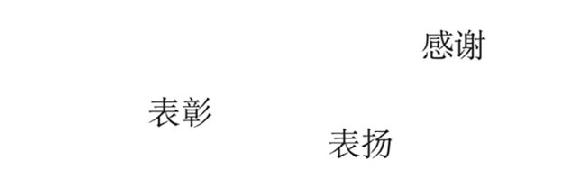
B班为国家所做的贡献。比利发现客人们都专心致志地听诺姆演讲,脸上的表情流露出信念与决心。男人们看上去睿智,轻松,人到中年依旧保持着良好的身材,透着成功人士与生俱来的自信与优雅。头发保养得很好,皱纹也恰到好处。女人们身材姣好,皮肤晒成了国际化的古铜色,厚厚的妆容上像是抹了一层冷漠的特氟龙涂层。比利想象着是怎样的出身、金钱、学校和阅历搭配在一起,成就了这些人今天高不可攀的地位。不管是什么,他们让这一切看上去如此简单,只是站在那里,只是在这个特殊场合做他们自己,暖和、安全、干净,做诺姆的座上宾。大部分人手上拿着饮料或端着食物。邪恶,诺姆说,恐怖。致命威胁。战争中的国家。他把形势讲得很严重,可是此时此地,战争似乎非常遥远。
“他们马上就要离开,”诺姆说,“等会儿要去参加中场秀,不过趁他们在这儿,让我们献上得州人最热情的欢迎。”大家鼓掌欢呼,让派对开始吧;来宾们感受到了B班的气息。一个满脸皱纹的老人家上前跟比利打招呼。
“士兵,很高兴见到你!”
“谢谢,先生。我也很高兴见到您,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