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 阿瑟 · 米勒国际笔会讲演词
1985年3月,阿瑟·米勒和哈罗德·品特一起来到伊斯坦布尔。当时,他们可能是世界戏剧界名头最响的两个人物。但是很不幸,他们来到伊斯坦布尔不是因为有什么戏剧或文学活动,而是因为当时的土耳其无情地限制言论自由,使很多作家在监狱里饱受折磨。1980年,土耳其发生了一次政变,成千上万的人被关进监狱。像往常一样,受到最残酷迫害的还是作家。现在,当我翻阅那时的存档报纸和年鉴,想了解那段日子的情况究竟是怎样时,我很快就能看到一些最为典型的形象:人们坐在法庭里,两边围着宪兵,这些人都剃着光头,随着诉讼的进行不停地皱眉。这些人里有很多是作家。阿瑟·米勒和哈罗德·品特来伊斯坦布尔,就是为了见他们以及他们的家人,并提供帮助,让全世界都关注他们的苦难。他们的这次来访,是由国际笔会——诗人、剧作家、编辑、散文家和小说家国际协会——与赫尔辛基监管会合力安排的。我去机场迎接了他们,因为我和一位朋友要给他们做向导。
有人推荐我来做这份工作,不是因为我那时和政治有什么牵连,而是因为,我是一个英语流利的小说家。而我之所以欣然答应,也不仅仅因为这能给身陷麻烦中的作家朋友们提供帮助,还因为我可以借此和两位文学巨人待上一两天。我们一起参观了处于挣扎之中的小出版社,黑暗、满是灰尘、濒临倒闭的小杂志总部,乱成一团的编辑部,还有那些受苦的作家与家人,他们的房子,他们常去的餐馆。在此之前,我只是站在政治世界的边缘,从来不想介入其中,除非是被迫而为。但是现在,当我听到那些令人窒息的关于镇压、残酷和邪恶猖獗的故事时,负罪感让我介入了政治,正如同踏实感也是让我介入政治的另一个因素。但是,同时我又感到一种同样强烈却与之相反的愿望:要保护自己免受政治之害。除了写优美的小说,我应该别无他求。我和我的朋友乘出租车带着米勒和品特,在城市的车流中穿梭,去参加一个又一个拜会。我们讨论街上的小贩、马车、电影海报以及戴围巾或不戴围巾的女人。她们戴不戴围巾对于西方的看客来说,总是那么耐人寻味。我对一件事情印象尤为深刻,直到现在,它还常常在我脑海中浮现。它发生在客人下榻的希尔顿酒店。在一个很长的走廊尽头,我和朋友有些激动地低声交谈着,而另一端,米勒和品特也在阴暗处以同样压抑的激动情绪在低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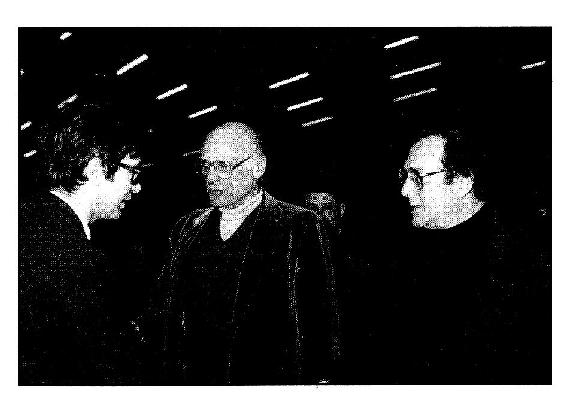
我们在参观过的每一个房间,都能明显地感觉到同样紧张的抑郁。在一个又一个房间里,困惑的男子一支接一支不停地抽烟,这是一种由自尊和负罪感营造出来的氛围。有时,这种感情会公开地表露出来;有时,我只能通过自己的感觉,或是从别人的手势和话语里体味到这种情绪。我们会见的作家、思想家和记者,多数都把自己当做当时的左派分子,因此可以说,他们的麻烦与西方自由民主国家所看重的自由有很大的关系。二十年过去了,当我看到现在这些人中有一半——或者大概有一半,我没有确切的数字——已加入了与西化和民主格格不入的民族主义同盟时,我当然会感到悲哀。而近来发生在中东的事件,已经让那些相信民主就是未来的人偃旗息鼓。
然而,当时做向导以及后来相类似的经历,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印象其实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现在,我想借此机会再次强调:不管处在哪个国家的环境之下,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都是普遍的人权。现代人对这些自由的渴求,不亚于处于饥饿中的人对面包的渴望。它永远不应受到限制,哪怕是打着民族主义情绪、道德敏感或者希求国际利益的旗号。如果西方世界以外的国家在耻辱中遭受着贫穷,那不是因为它们享有言论自由,而恰恰相反,那正是因为它们没有言论自由。但我们也会看到,那些为了逃离经济困难和残酷镇压而移民到西方或北方世界的人,他们有时会发现自己在富裕的国家里反而受到更残酷的种族主义虐待。对这些移民在西方,尤其是在欧洲所遭遇的仇外现象,我们一定要加以警惕。诋毁移民和少数民族的宗教、民族之根,或是诋毁他们身后的祖国让他们遭受了压迫,对这些倾向,我们也一定要加以警惕。但是,要尊重少数民族的人权,尊重他们的人性,并不是说我们应该容纳一切信仰,或者容忍那些为了尊重少数民族道德准则而攻击,或企图限制思想自由的人。我们中有些人对西方有较好的了解,有些人对生活在东方的人怀有更多的爱,有些人则像我一样想同时两者兼顾。但是,这种种关系,这种试图了解的愿望,都不应该成为我们尊重人权的障碍。
我向来难以非常清晰地表达出我的政治判断,我觉得很做作,似乎我在说的事情不是很真实。这是因为,我知道我必须把生活的想法转成单一声音的音乐和单一的视角。而我毕竟是一个小说家。我生活的世界,有些暴政和压迫的受害者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会突然变成压迫者。但我知道,保持坚定的信仰本身是很困难的,有时坚定的信仰本身就是背信弃义。的确,我还相信,我们大多数人都同时有矛盾对立的想法。写小说的快乐就来自于探讨这种很特别的现代思想状态——人们总是自我矛盾。因此我相信,言论自由非常重要。它让我们能够发现生活中被社会所掩藏的各种真理。同时,我从自己个人的经验认识到,我先前提到的耻辱和自尊,也有它们的作用。
让我再讲一个故事,它也许能解释二十年前我带着米勒和品特参观伊斯坦布尔时,我所感觉的耻辱和自尊。在他们来访后的第十年,我发现自己已经变成了一个很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我事前可没想到情况会这样。这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巧合、良好的愿望、气愤、负罪感和个人的忌妒,而根本不是因为我写的书,因为实际上,这与言论自由有关。大概就在此时,一位印度作家,赶到伊斯坦布尔来拜访我。他是一位上了年纪的绅士,是联合国派驻我们这里的言论自由报告团成员。碰巧,我们也是在希尔顿酒店见面。刚在桌前坐下,这位印度绅士就问了一个问题,那问题至今仍在我脑海里奇怪地回响着:
“帕慕克先生,你希望在小说中探讨你们国家正在发生的事情,却又避免卷入其中,是害怕受到起诉吗?”
接下来是一段长长的沉默。我被他的问题难住了,于是想啊想啊想啊。我陷入了一种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绝望。很明显,联合国来的这位先生想问的是,“考虑到你们国家的禁忌、法律禁令和高压政策,你的书里还有什么东西没说出来?”但是因为他——也许是出于礼貌?——已经要求坐在他对面的这位热切、年轻的作家就自己的小说来回答这个问题,所以缺乏经验的我只能按照字面的意思来理解他的问题。十年前,和今天相比,更多的题材被法律和国家的高压政策所禁止。当时我把那些题材一一想遍,却没发现任何我想“在小说里”进行探讨的题材。然而我知道,如果我说,任何我在小说里想写的东西我都可以谈,那么我又在给人一种错误的印象,因为,此前我已经开始经常吵吵嚷嚷,谈论我小说“之外”所有的危险题材了。甚至,就因为那些题材被禁,我不是还经常生气地幻想着要在小说里写那些题材吗?考虑完这一切,我立刻为我的沉默感到羞耻,然而却又深深意识到这一事实:言论自由与自尊心和人的尊严有关。